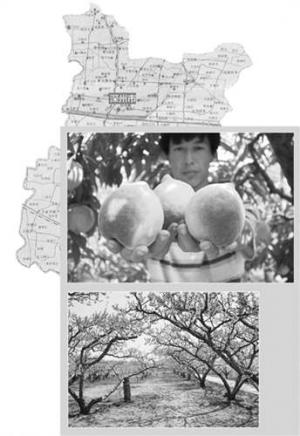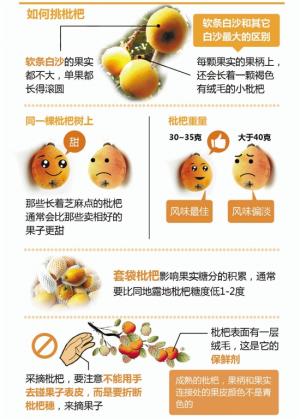香蕉之惑
施雁冰
这个故事,是一位女士对我说的。
她说,她年轻的时候,差点成了舞蹈演员。那年,她读初中,舞蹈学校的老师来学校物色学生,拿着皮尺在她身上横量竖量,很快就被录取了。不久,红色风暴席卷全国,录取通知单成了废纸。学校停课,她在宣传队里跳跳舞蹈,喊喊口号,觉得跟去舞蹈学校差不多,很是开心。
一天傍晚,她和两个伙伴迷了路,看见前方有座孤零零的白墙黑瓦房子,就到那里投宿。原来是个小火车站。值班的铁路工人正在吃炸酱面,顺手给她们弄了三碗。吃饱喝足以后,她们把地板踩得嗵嗵响,载歌载舞地表演起来。那工人也作了答谢。他的节目是舞剑。寒光闪闪,冷气逼人。她们看厌了。不可否认,水平很高。
这个小站有三间平房。工人值夜班,把她们安排在卧室里。还给了一串香蕉,说是亲戚送的。室内有张板床和简陋的白木方桌。一只油漆剥落的马桶,藏在屋角。
一天没有喝水,嘴巴燥燥的,待到门一关,三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猎物。香蕉黄澄澄,匀称鼓胀地一条条排列着,里面充满了汁水。正准备动手的时候,一个念头从她脑袋里跳了出来:“慢!他不认识我们,为什么要送香蕉?”
两个女孩也转动眼睛思索了: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他有什么企图?“我看他鼻子尖尖,很像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。又会舞剑,既可防身也能杀人!”她说。
“对!对!”伙伴们附和,“说不定香蕉里还放了毒呢!不然,他为什么自己不吃?”
朦胧的夜色中,香蕉仿佛突然萎黄了,鼓鼓地胀着毒液。
火车隆隆开过。悠远苍凉的汽笛声在夜空盘旋,形成一种恐怖的气氛。她们坐立不安,身子挤得紧紧的,小声地商量着。最后作出决定:消灭毒物,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她捧起香蕉,在屋内扫视一圈,眼光落在马桶上。两个伙伴踮着脚轻轻靠近,揭开马桶盖。一股骚气扑鼻而来。她屏住气,扑通一声掷下去,有一些污物溅出,赶忙把盖子盖紧。重重透一口气,三个人都笑了,认为是打了个胜仗。
“后来呢?”我问。
随着时光流失,人生花季的消逝,她有了感悟,觉得对不起那铁路工人。
“后来才认识到自己真傻!”她苦笑着。五十多岁,依然白皙修长,不减当年风韵,只是脸上有了细密的皱纹,眼角尤其明显。下岗,提早退休,赋闲在家,像重重阴影,压在眉梢。
说着,摇摇头,叹口气:“唉!真可惜!”
我不知道她可惜的是香蕉还是她自己。
这个故事,是一位女士对我说的。
她说,她年轻的时候,差点成了舞蹈演员。那年,她读初中,舞蹈学校的老师来学校物色学生,拿着皮尺在她身上横量竖量,很快就被录取了。不久,红色风暴席卷全国,录取通知单成了废纸。学校停课,她在宣传队里跳跳舞蹈,喊喊口号,觉得跟去舞蹈学校差不多,很是开心。
一天傍晚,她和两个伙伴迷了路,看见前方有座孤零零的白墙黑瓦房子,就到那里投宿。原来是个小火车站。值班的铁路工人正在吃炸酱面,顺手给她们弄了三碗。吃饱喝足以后,她们把地板踩得嗵嗵响,载歌载舞地表演起来。那工人也作了答谢。他的节目是舞剑。寒光闪闪,冷气逼人。她们看厌了。不可否认,水平很高。
这个小站有三间平房。工人值夜班,把她们安排在卧室里。还给了一串香蕉,说是亲戚送的。室内有张板床和简陋的白木方桌。一只油漆剥落的马桶,藏在屋角。
一天没有喝水,嘴巴燥燥的,待到门一关,三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猎物。香蕉黄澄澄,匀称鼓胀地一条条排列着,里面充满了汁水。正准备动手的时候,一个念头从她脑袋里跳了出来:“慢!他不认识我们,为什么要送香蕉?”
两个女孩也转动眼睛思索了: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他有什么企图?“我看他鼻子尖尖,很像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。又会舞剑,既可防身也能杀人!”她说。
“对!对!”伙伴们附和,“说不定香蕉里还放了毒呢!不然,他为什么自己不吃?”
朦胧的夜色中,香蕉仿佛突然萎黄了,鼓鼓地胀着毒液。
火车隆隆开过。悠远苍凉的汽笛声在夜空盘旋,形成一种恐怖的气氛。她们坐立不安,身子挤得紧紧的,小声地商量着。最后作出决定:消灭毒物,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她捧起香蕉,在屋内扫视一圈,眼光落在马桶上。两个伙伴踮着脚轻轻靠近,揭开马桶盖。一股骚气扑鼻而来。她屏住气,扑通一声掷下去,有一些污物溅出,赶忙把盖子盖紧。重重透一口气,三个人都笑了,认为是打了个胜仗。
“后来呢?”我问。
随着时光流失,人生花季的消逝,她有了感悟,觉得对不起那铁路工人。
“后来才认识到自己真傻!”她苦笑着。五十多岁,依然白皙修长,不减当年风韵,只是脸上有了细密的皱纹,眼角尤其明显。下岗,提早退休,赋闲在家,像重重阴影,压在眉梢。
说着,摇摇头,叹口气:“唉!真可惜!”
我不知道她可惜的是香蕉还是她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