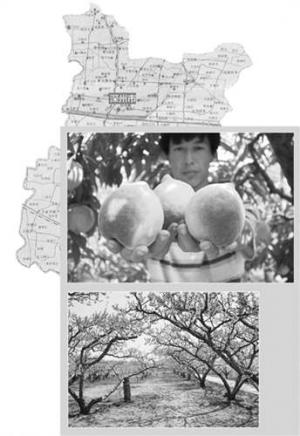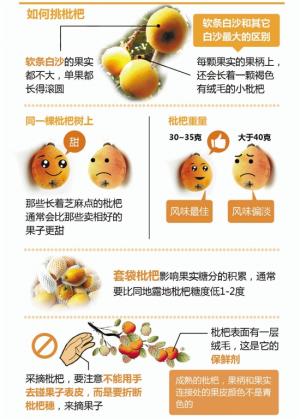榴花西来
作为象征物的石榴
古法语石榴(pome grenate),意思是“有许多种子的苹果”。古罗马的石榴树是婚姻树,新娘要头戴石榴树枝做成的花冠,它象征了爱情、婚姻和生育。中亚人在婚礼上砸碎石榴,来预测未来的生育状况……在世界各个民族的习俗中,大概没有一种水果能像石榴一样,让人们找到象征的共通性:丰饶、多子,一种生育的祝吉,如中国人所说的“榴开百子”。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集中在石榴“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”的特征上。可以说,石榴崇拜就是生育崇拜。
记载在《北齐书·魏收传》中的一则故事说:齐王纳李祖收的女儿为妃。一次,齐王赴李宅家宴,妃母送他两只石榴。王莫名其妙,问身边的人,也不解其意,就没要石榴。李祖收说:“石榴房中多子,王新婚,妃母欲子孙众多。”王听后大喜,要了石榴,还赐给李祖收美锦两匹。
从六朝开始,石榴就被中国人用作生子以及多子多福的祝吉之物。而石榴酒和葡萄酒的酿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,它们被用于上层贵族的婚宴上。在民间,婚嫁之时常常将切开果皮、露出浆果的石榴放置在新人的洞房里,以石榴祝多子成为一种习俗。除了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外,石榴纹图更多出现在剪纸、年画、文具、家具、什物上,与佛手、蝙蝠、寿桃等,构成了中国人的吉祥图案。
无独有偶,六七世纪的中亚有一个相似的风俗。撒马尔罕地区的新娘出嫁时要从娘家带一只石榴,婚礼后将石榴砸在地上,数一数从里面能蹦出多少石榴籽,以此来占卜自己的生育情况。在中亚地区的陶罐、壁画、锦缎等文物上,不乏石榴纹样和图案。包括现在维吾尔族的乐器和艾得莱斯绸,石榴是较常见的图案。历史上,石榴还是中亚拜火教徒们的圣物。他们手持石榴枝,口嚼石榴叶,来完成神圣的净化仪式。由于石榴包含的火焰般的光明特征,拜火教徒们认为,石榴是“生命树”,和西亚的香柏、中国的扶桑、印度的菩提树一样,是支撑宇宙的树。
在阿拉伯人的婚礼上,石榴主要用来告诫男人。新娘来到新郎的帐篷前,下马时首先接过一只石榴,将它在门槛上砸碎,把石榴籽扔进新郎的帐篷。这是在提醒男人,和平时期要像甜石榴一样温柔多情,战争时则如酸石榴一样呵护亲人并勇往直前。这使我想起格鲁塞对蒙古人的评价:“他们战时野兽一样冲锋陷阵,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,又像绵羊一样生产乳汁、羊毛和其它有用之物。”(《草原帝国》)
希腊人赋予石榴一种张力,一种埃利蒂斯所说的“光明的对称”。这与他们追求的精神与物质、理智与情感的和谐有关。石榴,既是奥德修斯的水手们在“忘忧果之岛”上吃到的“忘忧果”,又是大地女神的女儿帕尔塞福涅在冥府里无法拒绝的诱惑。“悲伤的果子,一旦品尝,禁梏我终生。”(罗塞蒂:《帕尔塞福涅》画上题诗)因此,在希腊人的理解中,石榴是解放与禁梏、忘忧与悲伤、诱惑与惩罚、光明与阴影的统一体——一种取消了二元对立同时又左右为难的水果:一个矛盾,一种困惑。
我曾把新疆绿洲称为沙漠中的“孤岛”,它们既是自足的乐土,又是地理的弃儿。河流的摆动和改道使绿洲变成一座座孤岛,不停地在沙漠里漂移、迁徙……许多绿洲已被沙漠无情吞噬。有关绿洲上人的生活状态,他们的习性、体貌,以及种种故事和细节,已不为我们所知。还有的绿洲被沙漠藏匿起来,几十年上百年地与世隔绝,在方圆几十公里或仅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自足的区域。他们的出产与消费,生存与死亡,泪水与欢笑,是那么有限和渺小,只需一小块绿洲就能装载。
那么像皮亚曼乡这样出产石榴的绿洲呢?它们仍是沙漠中孤独的岛屿,并没有被人们很好地理解和认识。石榴是孤独的树,在我们理解力之外生长、老去,然后死亡。石榴花如火如荼,石榴汁宛如琼浆,却在增加某种难言的孤寂和脆弱。因此在我眼里,石榴绿洲既是“忘忧果之岛”,又是“禁梏之岛”。
在世界诗歌中,有两首石榴诗令我十分难忘。它们是埃利蒂斯的《疯狂的石榴树》和瓦雷里的《石榴》。
埃利蒂斯的石榴树,代表了一种优雅的疯狂?是力与美的象征:夏天的石榴树急急忙忙解开白昼的绸衫,在阳光中撒播果实累累的笑声,惊醒了草地上裸体沉睡的姑娘们。石榴树高举它的旗帜,同宇宙间多云的天空零星地战斗,喻示一种新希望的破晓。瓦雷里笔下的石榴则是智慧的化身,一棵石榴树就是一个“智力的节日”。石榴因籽粒饱满而张开了口,宛若睿智的头脑被自己的思想涨破了头。瓦雷里认为人的灵魂像石榴一样,内部有着神秘的迷宫般的结构。
——在孤岛般的中亚绿洲上,一只只转动的石榴头颅正是一个个“智力的节日”!
来源:新疆经济报